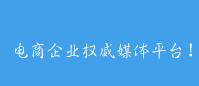大家读凯尔森的作品、阿克曼的作品、施米特的作品,会发现他们其实用的是不同的政治或者宪法时间。
实际上这本书storia就是历史,而Storia delle Costituzione Roma,就是《罗马宪法史》的意大利原文。我先给杜老师行一个礼吧。

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由谁共和呢?由周公和召公两位宰相级人物共同主持共和,所以共和制度这种两权两极的体制在中国周朝就存在了。后来,杜老师去汕头大学了,我自己才开始关注和研究儒家宪政。我们今天讲宪法制度,有哪些宪法制度可以和儒家联系起来思考呢?我们今天讲宪政,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代议制度、代表制度,它的理论的根据是什么?就是儒家的贤人政治。每日大家都不去生产不去干活了,都忙于政务?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管理者。
杜老师刚才还讲到了依法行政。管仲为齐国制定的宪法,它不仅包括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,也包括地方(刚才姚老师讲了这个地方自治)制度,以及军事组织、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,管仲之所以能够起草齐国的宪法,也是受到了洪范九畴这第一部宪纲、《周官》这第一部宪典的影响,同时又结合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宪法制度。我们需要安顿自己的内部,同时也要从人类去构想以及享受这种优良的政治生活。
刚才杜老师讲了,周公创制立法,他所创立的礼法就是周礼,周公之礼。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,就是两大类正常政体加上多数人执政,这三种政体变化以后,就是变态政体,君主变成了寡头、暴君,民主政体成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等等。为什么?就是因为蛮夷的不断入侵、冲击,使得这些地方的儒家文化已经很淡薄了。把政府的权力进行切割,又进行装配,让它们相互之间形成制约与平衡。
第三,我提出,中国的世界秩序想象是天下。所谓的民主政体,就是多数人执政的政体,但是儒家从来不是这样看问题的。

任何一个执政集团、执政者、个人,都不可以违法,不可以违宪,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。当然,你不能说这个看法不对,但是,它有严重的不足。在他这样回答的背后,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思考方法。主持人:接下来进入两位嘉宾互相对话和评议的环节,首先有请秋风老师对杜钢建老师的演讲做一个十分钟的评议对话。
杜钢建:非常高兴,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和老朋友姚中秋老师来讨论儒家宪政的话题,而且使我大为吃惊的是,见到姚老师以后,姚老师先把《华夏治理秩序史》这四部他个人的研究成果送给我。有朋自远方来,那么我们首先有请秋风老师讲演。你说古代韩国没有宪法制度,韩国人也会说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。进一步有后来的三省六部制,一直影响到隋唐甚至宋明。
所以为什么要谈谭嗣同,因为我和姚老师一样,我的学习体会是:传统文化最终要归结为谭嗣同讲的仁学。立政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民、保民,这是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。

他要维护学术自由,维护学术尊严,维护人格权利等等,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,这就是义道。你想想,这个宪法是一部成文宪法典的宪法?还是不成文的宪法性的法律组成的宪法体系?抑或是包括一些习惯、惯例、匾章、祖训等等的有关中央政府各种行为规则的宪法,还是这部宪法不仅要有现代讲的人权保证的概念,还要有像美国宪法典一样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?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,如果一个国家有正常的的统治秩序的话,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宪法,不管这部宪法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。
最后薛军老师反复斟酌,不敢翻译成宪法,翻译成了《罗马政制史》。它跟法治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,性质上没有任何差别。但是,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,用谭嗣同的话就是:百代皆行秦制。第四个就是政道,政治的政。儒家从来不相信全体人民同时都来主持国政,来商讨国政。很多对儒家、对儒家宪政概念的批评,都是因此而起。
那个活动之前,我对杜老师已经非常敬佩,因为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提出儒家宪政这样的概念,真的是石破天惊。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制度是自治。
第三个方面,我提出儒家宪政观念,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知识上的愉悦,为知识而知识,它是有一个现实的指向的。如果你看了这本书的内容就知道,他写的就是罗马宪法史,关于古代罗马的宪法制度、地方自治等方方面面。
如果只说权力分立的话,那么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是权力分立的。周公的重要贡献在制定宪法上,在他的主持下,又起草了《周官》,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宪典。
杜钢建:刚才秋风老师讲了一个如何看待中外古今的宪法的问题。所谓政道,一定要由它的宪法制度来确定政道。由所谓的兴利之臣,即建立和维护盐铁官营制度的大臣,和贤良文学之士共同进行审议,对一个一个问题逐个进行讨论、辩论。他们并不只是劝皇帝修身,他们设想了很多办法,力图用制度来控制皇帝,当然也制约各级官员的权力。
什么问题?大众媒体最近几年经常提及儒家宪政,很多人会问我,说:你提这个儒家宪政,究竟想干什么?你的意图是什么?你这个儒家宪政的蓝图是什么?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背景,就是蒋庆先生也提出了一个儒教宪政。由政府确认重大事项,把每日的活动记录下来、载明下来,就像我们历代的史书一样,这就叫文明。
梁启超开始把儒法分开以后,谁归为儒家,谁归为法家,有很多人就面临着被划分的困惑了。这样的努力才有可能让中国人不仅自己过上好日子,也对人类做出其应有的贡献。
有分离就会有制约,实际上,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制度性安排,使得皇权没有办法随意地、专断地行使自己的权力。比如,汉儒做的事情就出创制立法,他们解决问题,首先想到的就是制定制度。
法家讲法治吗?法家的人物非常复杂,讲术治的,讲权势的,玩权术的,各种都有。第二个是谁?就是周公。为什么会那样?一定是那时候的制度比较健全。在日本圣德太子是摄政王,当摄政王之前他对自己的身份是秘而不宣的。
总之,在董仲舒更化之后,形成了皇权与政府之间的分离。但他又把自己的概念看成可以普适的,而到处应用。
对儒家宪政还没有一个体悟。这个问题对于儒家宪政这个命题能不能成立,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
它们中间一定有很多相通的东西。什么原因呢?它非常简单,一共九条,条文简单但是思路清楚,而且它确立了宪法的根本原则。